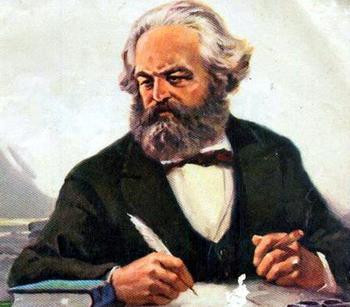从抗日战争中的学术人民化看“第二个结合”的威力
习近平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就说过,必须‘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探索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旗帜和灵魂。从本质特征上讲,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并不是简单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而是结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实现普遍性与特殊性、世界性与民族性有机统一中展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对此,我们可以追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源头,立足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载体——学术研究,聚焦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过程中,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广大学者开展学术研究,形成学术成果,进而深入研究和回答重大时代问题的。这对于推动当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价值。
一、学术探索的动力:唤起抗日救亡的民族精神
时代是学术出场的境遇。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危机加深,学术探索和研究的重点转向唤起民众的抗日救国热情。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在以铁蹄践踏中国国土的同时开启了“文化侵略”。为泯灭中国民众“反满抗日”的爱国意志,伪满洲教科书充斥大量颠倒黑白、宣扬“日满一体”“共存共荣”美化殖民统治的内容。青年学生“思想言论得不到任何的自由,强迫学日语,读经,尊孔,以及‘满洲国’的王道教育”。民族蒙难引发文明蒙尘的民族文化危机。一些有理想、抱负的爱国知识分子立民族救亡之潮头、通古今学术之变化,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路径,为拯救国家于危亡述学立论,发出了“伟大的抗战建国时代,正是中国学术开足马力的前进时代”的呐喊,并提出“学术就是为了这种需要而产生”“中国要从一个旧国家发展成一个新国家,当然在政治,经济,国防,文化等等方面都有很多的需要,这种需要都有待于近代学术的帮助解决。但外国的学术因外国的需要而产生而前进,未必能适合于中国的需要”。
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着力在学理上挖掘中华传统文化优秀基因,凝聚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精神力量。在忧患意识作用下,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适应抗日民族斗争形势,开始审视自身的民族文化。正如英国学者科恩所言,“一个社会群体只有在被逼到自身文化的边缘时,才又重新发现本身的文化,并对此文化重加评估”。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深深认识到“敌人不但要灭我们的国家,而且正在用种种方法想毁灭我们的文化,使我们在文化上也要成为他们的奴隶”,进而激发了学术救国的使命。“我们文化界的战士,必要明确不易地宣布,我们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的传统的继承者,我们不但要开来而且是要继往的”“凡是不甘中国文化被敌人所消灭的,凡是不愿中国过去的任何圣经贤传被敌人利用为愚弄同胞的工具的,都应该在这个大目标上团结起来……凡是孔孟最好的子孙,都是爱中华民族的,是和日寇不两立的”。面对抗战的激变局面,新启蒙者提出了构建新文化的设想,即我们“所要造的文化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外来西洋文化;也不应该只是固守本国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乃应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一种真正新的文化的产生,照理是由两种不同文化的接合,一种异文化(或说文明)的移植,不合本地的土壤,是不会生长的”。在抗战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从审视到扬弃的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着力于学术通俗化、大众化研究和传播,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抗战的思想武器。就时代背景而言,尽管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历经千辛万苦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但马克思主义仅在革命的先进知识分子头脑中落地生根,还没有在广大民众中广泛传播。为了“把世界上最先进的学术思想和中国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使高度抽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褪去神秘性,通过民族化的表达形式深入人心,以艾思奇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这在打破从来哲学的神秘观点上,在使哲学和人民的日常生活接近,在使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也知道注意哲学思想的修养上,是有极大意义的,而且这也就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通过学术通俗化、大众化的表达方式推介马克思主义,拉近了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亲近感,增进了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心理认同,在把马克思主义转化成抗日斗争思想利器的同时,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二、学术转化的场景:立足中国革命具体实际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出场主要源自批评和改造党内严重背离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照搬马克思主义“本本”的教条主义、完全服从“上级”指示的苏俄经验神圣化的错误思想路线。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首先要立足于中国即中国具体实际,特别是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还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角度出发,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途径,指出:“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体现了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从个体认知上升到政治自觉,这一命题由此成为抗日斗争的行动指南。
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指导,学术中国化也是从中国具体革命实际出发,进而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学理支撑。“学术中国化运动,是伴随着学术通俗化运动,或大众化运动而生长出来的……随着‘七七’抗战的兴起,这个运动更加速的进展,直到最近,‘中国化’这个口号乃在这个运动的高潮中很有力地涌现出来。”学术中国化是为了回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对外来文化进行中国化的学术探索与实践,既是抗战时期政治路线在学术领域的反映,又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关于学术中国化的动因,柳堤强调,学术中国化“绝不仅限于纠正过去我们对外来文化的不溶化,纠正我们学习上、学术上许多公式主义,教条主义,给我们一种警惕,而是创造新的中国文化之行动的口号和前提”。为了使学术适合中国的需要,一方面,“要在学术思想领域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去研究中国历史,中国问题,一切的问题”;另一方面,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在中国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吸收一切进步的文化,溶化它,通过民众的特点,历史的条件,中国抗战建国过程中的一切具体问题,把它变为我们自己的灵魂,‘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对此,杨松指出:“坚持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坚持自己对于科学的共产主义信仰,而应用马列主义的思想武器,应用马克思和列宁的唯物辩证法,去批判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为建立以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为内容和以中华民族的形式为形式的中华民族文化,并且在中国历史学、政治经济学、哲学、文学、音乐、美术、戏剧、诗歌和自然科学中,获得、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地位。”
三、学术运用的场域:话语权的争夺与博弈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展开政治博弈的重要表现就是争夺学术话语权。而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的对话、交锋,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学术场域。抗战时期,尽管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统一战线中摒弃前嫌、携手合作,但国民党一直没有放弃全面打压中国共产党的企图。随着1939年国民党出台“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一批依附于国民党的学者基于自身立场,开始在学术上摇旗呐喊,以学术理由和借口大肆抹黑、污蔑中国共产党。如何有力捍卫真理,打破国民党反动学术蛊惑,使思想陷入沉睡状态的国人彻底清醒,是推动抗战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
抗日战争时期,关于怎样正确看待古今文化和中西文化问题,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学术论辩的焦点。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国民党御用学者曲解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怀疑、诘难和反对学术中国化问题。例如,叶青指出:“中国化是说欧洲乃至世界各国底学术思想到中国来要变其形态而成为中国底学术思想,这在哲学、社会科学和艺术方面,特别要如此,就中以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社会思想为尤甚。所以中国化是一般的或外国的学术思想变为特殊的中国的学术思想的意思。它必须变其形式,有如一个新东西,中国的东西,与原来的不同。这样才叫做化,才叫做中国化。所以化是带有改作和创造之性质的。理解、精通、继承、宣传、应用、发挥……都不是化,当然也都不是中国化了。”叶青对学术中国化发难,本质上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学术的指导地位,正如他所说,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中国,作为它底经济学基础的资本论、政治学基础的国家论、社会学基础的阶级斗争论便亦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是不需要共产主义,不需要马克思主义的了。因此它也就不需要共产党,这是逻辑的结论”。周宪文声称:“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对的,是适于目前的中国的,那我们就得毫无保留地把它移植过来,无法取其一部分,或改头换面而使它中国化。”上述观点均以切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为立足点,攻击学术中国化。
面对现实,中国共产党积极进行话语权的学术论争,以捍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针对国民党御用学者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法性,“要想从战斗的中国人民的手中,夺取最锐利的科学思想的武器”,以艾思奇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勇敢亮剑,对错误观点进行了坚决驳斥与批判。针对叶青等人歪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言论,艾思奇指出,“在口头上窃取把握特殊性的名词,故意将这一点夸大,抹杀了一般,结果在实际上正是反对正确地来把握中国的特殊性,反对真正把握特殊性的科学方法”,“‘国情论’中打扮得最时髦而表现得最下流的一个标本”,其本质在于“借特殊的名义,而把一般的科学规律完全丢掉”。他同时强调“坚持马克思、恩格斯所发现的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的科学规律,承认它有一般的指导的作用,而同时却一刻也不能忘记,这些规律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中间,因着客观条件的差异,而有着各种各样特殊的表现形式”。艾思奇以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为例,通过事实说明学术中国化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必然选择。
总之,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与国民党学者错误论点的交锋中,通过掌握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立场,为夺得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学术自觉的体现:学科研究范式创新
抗日战争时期,学术中国化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广泛应用于各学科领域,生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新的学术研究范式。中国共产党自觉把唯物辩证法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展现了学术研究的崭新风貌,尤其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具有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生成。
来自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冲破地域界限和民族藩篱,在中华大地上形成具有中国风格的学术范式,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文化、中国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心理相结合,结出了具有中华民族风格的学术硕果,进而为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学理支撑。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变革,不仅是中国语言表达的转换,更重要的在于理论创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哲学研究需要立足于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等时代之问,回答政治思想领域“古今中西”的学术之问。要解决这些难题,就必须构建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并真正应用于实践。这种全新的研究范式必然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例如,认识论研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怎样正确理解物质和意识、知与行的关系,对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认识基础上,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升华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毛泽东指出:“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冯契认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基础上,实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即把“认识论上的心物之辩和历史观上的心物之辩结合为一。《新民主主义论》用‘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来概括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也用它来概括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这一概念,极好地体现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统一”。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相统一的哲学研究范式,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性,又契合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特殊性,给予中国传统哲学“心物”之辩、“理气”之争以创造性解答。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继承发展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上,实现了本土化和民族化的研究范式创新。
第二,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中国特色史学研究方式的呈现。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残暴的殖民统治,利用现成学术研究以及歌颂帝王将相的史书,已经无法唤醒中华民族自信、自强、自主意识。伟大的民族斗争迫切需要通过中国史学研究鉴古知今,建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精神防线。为此,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史学研究工作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开展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史学研究,形成了史学为现实服务的全新研究方式。
抗日战争对学术的需要,使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研究势在必行。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通史的撰述,因为史学研究的唯物史观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历史的基本主张和看法。针对这种情况,延安、重庆等地史学家开始用中国话语体系阐释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并将其同中国史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形成史学研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方法。郭沫若在《历史人物》中,把唯物史观中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相结合,通过大量史料说明劳动人民在社会物质财富创造和精神财富生产中的重大作用,否定唯心史观中帝王将相创造历史的观点,开创了从人民史观角度出发开展史学研究的先例。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坚持了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直接动力的核心观点,以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为例,从中国历史经济关系的变化和阶级变化入手,揭示了私有制的本质,阐明了整部中国历史中阶级斗争的历史,纠正了立足统治阶级立场诋毁农民起义的偏颇认知,肯定了阶级斗争的进步历史作用,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士气。翦伯赞在史学研究中始终坚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以史为鉴、以笔为器、谈古论今、针贬时弊。他撰写《两宋时代汉奸及傀儡组织》等文章,立足唯物史观阐释了社会历史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重要观点,以历史上耳熟能详的卖国贼秦桧、张邦昌等民族败类为例,说明每当民族遭遇侵略时,总有部分汉奸主张妥协投降,甚至不惜做敌人的帮凶,阻挠反侵略战争。不同时代的汉奸尽管卖国行径各有不同,但与汪精卫之流出卖民族、出卖国家的本质如出一辙。
总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呈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和政治的双重价值。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对唯物史观史学的创新研究并不是纯理论的,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实现对历史批判与对现实洞察的统一,进而建构中国特色史学的学术体系。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历史有了全新的理论阐释,为指导抗日战争提供了历史借鉴。
第三,中国特质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风格日益凸显。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学术探索,既是对重大时代问题的回应,也体现了解决教条化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的理论自觉。对于在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土壤中孕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适用于抗日战争时期非资本主义经济占主导地位国家这一问题,王亚南、许涤新等经济学家坚持承继性和创新性的统一,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经济现实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在炮火纷飞的抗日战争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积极践履经邦济世、经民卫国的使命,满怀热忱地通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来为民族救亡图存道路提供理论指导。1938年,王亚南、郭大力合作翻译了三卷《资本论》,在中华大地上揭开了资本剥削劳动的神秘面纱,展露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使国人开始了解并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非翻译文本、照搬经典,而是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致力于研究“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阅读,特别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经济理论教程”,以“中国人的资格”“创建一种专为中国人攻读的政治经济学”。对此,王亚南指出:“我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文句、自己的写作方法,建立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同改造中国落后的经济现实相结合,在总结中国经济史实特殊规律的基础上,出版了以《中国经济原论》等为代表的大量具有中国特质的著作、文章,解答中国经济问题。《中国经济原论》被学界誉为“中国的《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该书继承了《资本论》的研究方法,透过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剖析地主经济封建生产方式,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运动的主体是商业资本,而非资本主义社会中直接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产业资本,深入总结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土地资本在中国历史中的发展规律,揭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畸形经济形态的本质,指出了中国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逻辑。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不仅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重大经济问题,而且致力于为解释和宣传党的经济政策提供学理依据,服务于中国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建设。许涤新在《新民主主义经济论》中分析了传统中国土地制度的不合理状况,论证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平分土地”等土地政策的可行性和合理性,为党的土地政策提供了理论解释力,提升了政治影响力。
总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不仅翻译宣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而且建构了自成系统的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理论体系,彰显了具有中国特质的理论研究风格。
第四,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蔚然成风。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导致的民族苦难,引发了中国文学工作者用文学力量捍卫民族尊严的强烈爱国热情。罗家伦指出:“感谢日本的飞机大炮,把我们散漫的民族,轰炸成铁的团结,把我们沉迷的大众,轰炸得如梦方醒,把我们衰弱颓废的思想,轰炸得烟消云散;——不把我们包裹重重的脓血炸开,哪有新的肌肉产生?”广大文学工作者纷纷通过文学创作投身伟大的反侵略战争,“但是在实际的服务工作中,文学和艺术碰了很多钉子,尤其是当文学和艺术要深入到广大的民众和士兵中去的时候,它们——文学和艺术碰的钉子更不少。仔细检查,碰钉子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被确认了,这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的文学艺术,正缺乏中国多数人所熟悉的、或容易接受的那种民族形式”。这就要求在抗战烽火洗礼中成长的中国文学,要从民族土壤中焕发生机和活力,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正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成就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的中国气派。
构建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文学,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转化为抗战文学理论与实践,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引领抗战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实践,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民族文化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中,形成文学研究的中国风格。文学工作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文学研究与创作中,立足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创造者的观点,阐明了文学艺术如何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本质要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提出:“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抗日战争时期,文艺宣传要深入人口众多但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中去,只有采取劳苦大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才能被农民所认同,发挥抗日文学精神食粮的作用。“最浓厚的中国气派,被保留、发展在中国多数的老百姓中。你没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老百姓决不会相信你的领导。你一站到民众中去,你一讲话、行动,老百姓可以立即分辨出你有没有中国味;正如听惯了平戏的人他一听得有人唱平戏,就会立即感觉那有没有平戏的味儿。”文学艺术民族形式的构建具有历史承继性,是在吸收和借鉴中华优秀文学艺术形式基础上创新发展的。对此,茅盾指出:“要吸收过去民族文艺的优秀的传统,更要学习外国古典文艺以及新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品的典范,要继续发展五四以来的优秀作风,更要深入于今日的民族现实,提炼熔铸其新鲜活泼的素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坚持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立场,提出构建文艺的民族形式。抗日战争时期,以弘扬人民群众不畏强暴为主题的具有鲜明民族形式的文艺作品不断涌现,如《小二黑结婚》《白毛女》等,形成了“人民文学洪流”。不论是与封建势力抗争的小二黑,还是从屈辱到反抗的白毛女,都反映了抗战时期人民群众不再愚昧、麻木,而开始真正成为社会历史变革的主体。抗日战争时期文学研究与创作正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吸取了民族文化的精华,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的中国气派。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彰显出中国风格、中国特质、中国气派。当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上,我们应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命题、范畴和标识性概念与范式,建构能够反映中国立场的自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用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回应重大时代问题,不断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
|
|
|
|
|
|
|
|